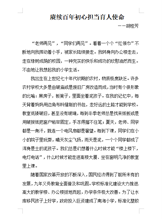老铜锁的时光絮语
我是一把老铜锁,在李家祠堂的木柜上挂了整整八十年。
我的身子是黄铜铸的,锁芯里嵌着细密的铜齿,锁鼻上还刻着一朵歪歪扭扭的莲花 —— 那是李家第三代传人老李头的爷爷,亲手刻上去的。八十年风风雨雨,把我的身子镀上了一层暗褐色的包浆,摸上去滑溜溜的,像浸过岁月的油。
我记得刚被打造出来的那年,李家还是村里的大户人家。祠堂里的木柜,装的是李家的传家宝 —— 一套缂丝屏风,还有几卷泛黄的古籍。我的任务,就是守着这些宝贝,不让闲杂人等碰分毫。那时候,每天傍晚,老李头的爷爷都会用一块软布,仔仔细细擦我的身子,擦完了,还会对着我念叨:“锁啊锁,你可得把咱家的宝贝守好喽。”
那时候的村子,安静得很。祠堂外的老槐树,叶子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。蝉鸣一声高过一声的夏天,总有穿着粗布褂子的孩子,扒着祠堂的门缝往里瞧,嘴里嚷嚷着:“里面有啥宝贝呀?” 我听见老李头的爷爷在里面笑:“有祖宗的念想哩。”
后来,世道变了。村里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往外走,有的去了城里打工,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上学。李家的人也少了,祠堂的门,十天半个月才开一次。老李头的爷爷走了,老李头的父亲接了班,还是每天擦我一次,只是念叨的话变了:“锁啊锁,啥时候咱家的缂丝手艺,能有人接班呢?”
我知道他说的缂丝手艺。李家祖上是做缂丝的,那套缂丝屏风,就是祖上的心血。缂丝这活儿,费眼又费神,一根丝线要劈成八瓣,在织机上一梭一梭地挑,一天下来,也就织巴掌大的一块。年轻人嫌枯燥,没人愿意学。
老李头的父亲走后,老李头接了班。他是个倔老头,头发白了,腰也弯了,却非要守着祠堂,守着那台老织机。他也每天擦我,擦着擦着,就会叹气:“锁啊锁,这祠堂,怕是要败在我手里了。”
我看着他把那套缂丝屏风小心翼翼地取出来,对着阳光看上面的纹路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我看着他把那台老织机擦了又擦,却再也没动过梭子 —— 他的眼睛花了,手也抖了,再也织不出那些细密的花纹了。
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。土路变成了水泥路,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楼。祠堂周围,盖起了农家乐,每天都有游客说说笑笑地经过。有人看见祠堂的老木门,就问老李头:“大爷,这祠堂里有啥宝贝呀?开门让我们瞧瞧呗。” 老李头总是摇摇头:“没啥宝贝,都是些旧东西。”
我知道,他是怕那些游客,把他的宝贝弄坏了。
有一天,祠堂里来了个小姑娘。她扎着马尾辫,穿着粉色的连衣裙,手里拿着一个相机。她是老李头的孙女,从城里回来的。她绕着祠堂转了一圈,眼睛亮晶晶的:“爷爷,这台织机好漂亮啊!”
老李头的眼睛亮了亮,又暗了下去:“漂亮有啥用?没人学喽。”
小姑娘却蹲在织机前,伸手摸了摸那些丝线:“爷爷,我学!我想学缂丝!”
老李头愣住了,过了好半天,才颤巍巍地伸出手,摸了摸小姑娘的头:“娃啊,这活儿苦,你受得了吗?”
小姑娘用力点点头:“我受得了!”
从那天起,祠堂里又响起了梭子的声音。小姑娘每天都来,跟着老李头学劈线、穿综、挑梭。她的手指被丝线勒出了红印,眼睛也熬红了,却从来没喊过一声苦。
我看着她,在织机前坐了一天又一天。看着她织出的第一片缂丝,虽然纹路还有些歪歪扭扭,却透着一股鲜活的劲儿。看着老李头站在她身后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游客们听说村里有人学缂丝,都跑来瞧。他们看着小姑娘灵巧的双手,看着那些丝线在织机上变成美丽的花纹,都忍不住啧啧称赞。有人问小姑娘:“你这么年轻,为啥要学这老手艺啊?”
小姑娘抬起头,笑了:“因为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,我想让它一直传下去。”
我看着她,看着她手里的梭子飞快地穿梭,看着那些细密的丝线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忽然觉得,我这把老铜锁,守了八十年,守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,而是一份念想,一份传承。
现在,祠堂的门,每天都开着。游客们可以进来,看小姑娘织缂丝,看老李头讲那些老故事。我的身子,还是每天被擦得干干净净。只是老李头念叨的话,变了:“锁啊锁,咱李家的手艺,后继有人喽。”
风从祠堂的窗缝里吹进来,带着槐花的香味。我挂在木柜上,静静地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,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,看着那些鲜活的笑容。
我知道,时光会流逝,岁月会变迁,但有些东西,永远不会变。就像这缂丝的手艺,就像这祠堂的老木门,就像我这把老铜锁,守着的,是岁月的痕迹,是传承的温度。
八十年的时光,在我身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。我是一把老铜锁,我守着李家的祠堂,守着一份永不褪色的念想。我知道,这份念想,会像这老槐树的根,深深扎进这片土地里,一代一代,永远传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