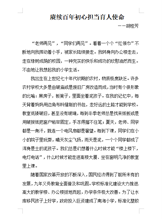巷口的糖画摊
清晨的风裹着巷子里特有的烟火气,慢悠悠地飘过来,我挎着菜篮子,踩着青石板路往巷口走,老远就看见那个熟悉的糖画摊,木头架子支着,玻璃罩子擦得锃亮,里面摆着几只晶莹剔透的糖龙、糖凤,在朝阳底下闪着琥珀色的光。
我是个退休的中学美术老师,今年六十七岁,每天早上最惬意的事,就是来巷口买两块钱的糖画,顺便和摊主张大爷唠唠嗑。张大爷的糖画摊在这巷子里摆了快四十年了,从我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时,就守着这个摊子,守着一锅熬得金黄的麦芽糖,守着老城南人心里最甜的念想。
张大爷今年七十有二,背有点驼,双手却依旧稳当。他的手指粗粝,布满了老茧,指关节因为常年捏着糖勺,有些变形,可就是这双手,能把滚烫的糖稀玩出花来。只见他从煤炉上提起熬得冒泡的糖锅,手腕轻轻一转,金黄的糖稀就像有了生命,顺着铜勺的边缘流下来,落在光溜溜的青石板上。手腕起落间,一道流畅的弧线划过,是龙的身子;指尖一顿,点出两个圆,是龙的眼睛;再轻轻勾几笔,龙的鳞甲、龙须就活灵活现了。不消半分钟,一条威风凛凛的糖龙就成型了,张大爷拿起一根竹签子,往糖画底下一粘,轻轻一揭,糖龙便腾空而起,脆生生的,引得旁边围观的小孩子拍手叫好。
“张大爷,今儿个生意不错啊!” 我笑着走过去,把菜篮子放在摊子边。张大爷抬起头,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,“李老师来啦!快坐快坐,刚熬好的糖稀,给你做个你最爱吃的蝴蝶。”我摆摆手,“不用不用,我就买个小兔子,给我那小孙女带回去。”张大爷也不推辞,拿起糖勺就开工。他的动作行云流水,仿佛不是在做糖画,而是在画一幅水墨画。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,忽然想起小时候,也是这样一个清晨,我攥着妈妈给的五毛钱,踮着脚尖看张大爷做糖画。那时候的糖画才两毛钱一个,可却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奢侈的零食。每次拿到糖画,我都舍不得吃,举着它在巷子里跑,引得一群小伙伴跟在后面追,阳光洒在糖画上,甜得晃眼。
这些年,巷子变了好多。矮矮的瓦房变成了青砖黛瓦的仿古小楼,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青石板路,就连巷口的小卖部,都改成了洋气的便利店。只有张大爷的糖画摊,还守在老地方,像一个固执的符号,提醒着我们那些逝去的时光。
前阵子,巷子里来了几个年轻人,拿着相机对着糖画摊拍个不停。他们说,要把糖画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,还要帮张大爷开直播,让更多人看到老手艺。张大爷听了,笑得合不拢嘴,却又连连摆手,“我这手艺,不值当那么大阵仗。只要还有人爱吃,我就一直摆下去。”
其实我知道,张大爷心里是盼着有人能继承这门手艺的。他的儿子在城里开了公司,劝他搬过去享清福,他不肯。他说,这锅糖稀,这根糖勺,就是他的根。这些年,也有几个年轻人来拜师,可都没坚持下来。熬糖稀是个苦差事,得守在煤炉边,盯着火候,一不小心,糖稀就熬糊了。画糖画更是个技术活,手腕的力道、速度,都得拿捏得恰到好处,差一点,画出来的东西就没了灵气。
那天下午,我又去了糖画摊。夕阳把张大爷的影子拉得很长,他正低着头,教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握糖勺。小男孩学得很认真,小手紧紧攥着勺子,小心翼翼地把糖稀淋在石板上。虽然画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,像一条小蛇,可张大爷却笑得满脸皱纹,一个劲儿地夸,“好,好,有天赋!”
晚风拂过,带着糖稀的甜香。我看着夕阳下的一老一小,看着那锅咕嘟冒泡的糖稀,忽然觉得,这门老手艺,就像这糖稀一样,虽然历经岁月的熬煮,却依旧甜得纯粹,甜得温暖。它不仅仅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种情怀,一种传承,是老城南人心里,永远割舍不掉的人情味。
巷口的路灯亮了起来,暖黄的光洒在糖画摊上,洒在张大爷和小男孩的身上,也洒在那些晶莹剔透的糖画上。我想,只要这糖画摊还在,这条巷子的烟火气,就永远不会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