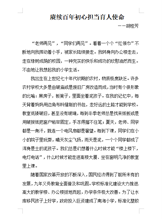巷口的糖画摊
清晨的风裹着巷子里油条的香气,溜过青石板路的缝隙,我揣着兜里皱巴巴的五块钱,三步并作两步往巷口跑——那里有张大爷的糖画摊,是我整个童年里最甜的念想。
我是个在老街长大的留守儿童,爸妈在南方的工厂里打工,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能回来。爷爷奶奶忙着打理巷尾的小菜园,大多数时候,我都是被丢在巷口自己玩。第一次遇见张大爷,是在一个蝉鸣聒噪的夏日午后,我蹲在墙角看蚂蚁搬家,被一阵叮叮当当的铜铃声吸引。抬头时,就看见梧桐树下支着的小摊,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上,摆着一个布满铜锈的糖锅,锅里琥珀色的糖稀咕嘟咕嘟冒着泡,一个穿着灰色对襟褂子的老人,正握着长长的铜勺,在光滑的青石板上龙飞凤舞。
“丫头,要不要来个糖龙?” 老人的声音像晒暖的棉花,软软的。我攥着空空的口袋,往后缩了缩脖子。他却笑了,舀起一勺糖稀,手腕一转,金红的糖丝便在石板上勾勒出龙的轮廓,眨眼间,一条昂首摆尾的糖龙就成型了。他用竹签一挑,递给我:“不要钱,尝尝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吃糖画,甜丝丝的味道从舌尖漫到心里,连带着夏日的燥热都消散了大半。从那以后,巷口的糖画摊就成了我的根据地。张大爷的摊不大,却藏着整个江湖。他的手很巧,铜勺在他手里像有了灵性,手腕轻转,便是孙悟空的金箍棒,再勾几笔,就是活灵活现的小兔子。路过的大人小孩都爱围在摊前,有人要威风凛凛的老虎,有人选憨态可掬的小猪,张大爷从不嫌烦,总是笑眯眯地问:“小朋友,今天想要个啥?”
我最爱看他熬糖稀。白砂糖和麦芽糖在锅里慢慢融化,从细碎的颗粒变成浓稠的糖浆,颜色从乳白变成浅黄,再到透亮的琥珀色。火候要刚刚好,火大了会糊,火小了糖丝拉不长。张大爷熬糖的时候,眼睛总是眯着,像是在琢磨什么宝贝。他说,这门手艺是他爷爷传下来的,到他这辈,已经是第三代了。“以前啊,这糖画摊能养活一家人呢。” 他一边说,一边用铜勺在石板上画着,“现在的孩子,都爱买那些包装花哨的糖果,没人稀罕这老玩意儿了。”
我那时候听不懂他话里的失落,只知道每次放学,都要绕到巷口,看他画一会儿糖画。有时候,我会帮他递竹签,或者帮他收拾摊前的小凳子。他会教我怎么握勺,怎么控制糖稀的流速。我笨手笨脚的,总是把糖丝画得歪歪扭扭,他也不恼,只是摸着我的头说:“慢慢来,这手艺,得沉下心。”
有一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,青石板路结了冰。我缩着脖子跑到巷口,却没看见张大爷的身影。我心里空落落的,一连几天都守在巷口,直到第五天,才看见他推着小车慢慢走来。他的脸冻得通红,手上裹着厚厚的棉手套,糖锅上盖着厚厚的棉被。“丫头,等急了吧?” 他笑着,掀开棉被,糖锅里的糖稀还冒着热气,“天冷,糖稀容易凝固,我得守着锅,不敢走远。”
那天,他给我画了一只小兔子,兔子的耳朵长长的,眼睛圆圆的,特别可爱。他说:“这个送给你,算是赔罪。” 我捧着糖画,心里暖暖的,连手都不觉得冷了。
后来,我上了初中,搬到了镇上住,很少再回老街。偶尔放假回去,也会绕到巷口,却再也没看见张大爷的糖画摊。听邻居说,张大爷的儿子接他去城里住了,糖画摊也被收起来了。“那手艺,怕是要失传咯。” 邻居叹了口气,“现在的年轻人,谁还愿意学这个。”
我心里一阵难过,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我想起那个蝉鸣的午后,想起他手里的铜勺,想起石板上活灵活现的糖画,想起那甜甜的味道。
前几天,我回老街办事,意外地在巷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穿着干净的白衬衫,正握着铜勺,在石板上画糖画。他的身边,摆着一块蓝布,上面写着 “张氏糖画”。我走上前,看见他手里的铜勺,和记忆里张大爷的一模一样。
“你好,要来个糖画吗?” 小伙子笑着问我,声音很爽朗。“你是…… 张大爷的徒弟?” 我忍不住问。“不是,我是他孙子。” 他挠了挠头,“我爷爷说,这手艺不能丢,让我回来继承他的摊子。”
他舀起一勺糖稀,手腕一转,一条金红的糖龙便在石板上成型了。阳光洒在糖画上,闪着晶莹的光,和我记忆里的模样,一模一样。
我买了一个糖龙,咬了一口,还是熟悉的甜味。风从巷口吹过,带着油条的香气,和糖稀的甜香。我仿佛看见,张大爷站在梧桐树下,笑眯眯地看着我,手里的铜勺,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
原来,有些温暖,就像糖画的甜味,永远不会消散。原来,有些手艺,总会有人记得,总会有人传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