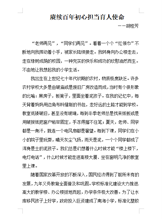巷口糖画摊的暖光
暮色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,慢悠悠地盖住巷口的老槐树,树影婆娑里,那个支着木架的糖画摊,又亮起了昏黄的小灯。我揣着兜里皱巴巴的五块钱,踩着放学路上的碎步,第三次往摊前凑 —— 这是我这个月最心心念念的地方。
我是个刚上初二的学生,每天放学都要路过这条老巷,而这个糖画摊,是巷口最热闹的风景。摊主是个姓陈的老爷爷,大伙儿都叫他陈糖匠,脸上的皱纹像被岁月揉皱的糖纸,笑起来却格外清亮。他的摊子简单得很,一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板,一个熬糖稀的小铜锅,一把长柄的铜勺,再加上一个插满糖画的草把子,就构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小天堂。
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摊子,是因为同桌小胖的一声惊呼。那天放学,小胖攥着一根糖龙,举得老高,糖衣在太阳底下闪着琥珀色的光,馋得我们几个围上去直咂嘴。小胖得意地说:“陈爷爷的糖画,能拉出丝来,甜到心窝窝里!” 我当时兜里只有妈妈给的两块钱,怯生生地凑过去,陈爷爷看我眼巴巴的样子,笑着舀起一勺糖稀,手腕轻轻一转,青石板上就出现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。“孩子,送你的,下次再来照顾爷爷生意。” 他的声音像熬得恰到好处的糖稀,温温柔柔的,裹着一股暖意。
从那以后,我就成了糖画摊的常客。有时候是五块钱买一条威风凛凛的龙,有时候是三块钱换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,更多的时候,是和几个同学围在摊前,看陈爷爷的 “魔术表演”。熬糖稀是个技术活,得用小火慢慢煨,铜锅在炭火上转着圈,糖块渐渐融化,变成粘稠的琥珀色,空气中飘起一股甜丝丝的香气,勾得人肚子咕咕叫。陈爷爷握勺的手稳得很,手腕翻转之间,糖稀像一条金色的小溪,在青石板上流淌、盘旋,不消片刻,一只展翅的蝴蝶就成型了,再用一根竹签往上一粘,轻轻一揭,一个晶莹剔透的糖画就做好了。
有一次,我看见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妹妹,站在摊前不肯走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草把子上的糖凤凰。她妈妈在一旁叹气:“家里糖太多了,不能再买了。” 小妹妹的嘴一撇,眼看就要哭了。陈爷爷放下手里的铜勺,笑眯眯地说:“丫头,爷爷给你画个小蝴蝶,不要钱。” 说着,手腕一抬,一只小巧的蝴蝶就出现在石板上。小妹妹破涕为笑,接过糖画,蹦蹦跳跳地走了。我问陈爷爷:“您这样不亏吗?”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,说:“做手艺的,图的不是赚多少钱,是看着孩子们开心,心里就暖和。”
日子一天天过去,巷口的老槐树落了叶又发了芽,陈爷爷的糖画摊,始终守在暮色里。我渐渐发现,来摊前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孩子,还有不少大人。有个叔叔,每次来都要一个糖老虎,他说:“小时候我妈总带我来买糖画,现在我妈不在了,吃着陈爷爷的糖画,就像回到了小时候。” 还有个阿姨,抱着刚会走路的小娃娃,指着糖画说:“妈妈小时候也爱吃这个呢。” 原来,陈爷爷的糖画,不仅甜了我们的童年,还甜了一代人的回忆。
可是,有一天放学,我路过巷口,却发现糖画摊不见了。青石板上空空如也,只有老槐树的影子,孤零零地躺在地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像丢了什么宝贝。后来听邻居说,陈爷爷的儿子接他去城里住了,说城里条件好,不让他再摆摊了。我心里空落落的,一连几天,放学都绕着巷子走,不敢看那个空荡荡的角落。
就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陈爷爷的时候,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又在巷口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陈爷爷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守着他的糖画摊,铜锅里的糖稀,正冒着热气。我惊喜地跑过去,他看见我,笑着说:“孩子,我回来啦。城里住着不习惯,还是喜欢和你们这些小娃娃待在一起。” 原来,陈爷爷在城里待了没几天,就惦念着巷口的老槐树,惦念着那群等着吃糖画的孩子,硬是让儿子把他送了回来。
那天,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,买了一个最大的糖龙。糖龙在阳光下闪着光,我咬了一口,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化开,一直甜到心里。暮色降临,陈爷爷的小灯又亮了起来,暖黄的光,照亮了巷口的路,也照亮了我们这群孩子的童年。
这个小小的糖画摊,就像巷口的一盏灯,用甜甜的糖稀,熬煮着人间的烟火气。它没有超市里的糖果精致,却藏着最朴素的人情味,藏着一个老人对手艺的坚守,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。原来,最温暖的味道,从来都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这样一份带着烟火气的甜,一份藏在巷口的,人与人之间的善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