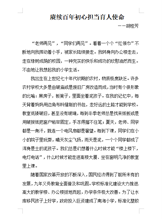老街的樟木箱
我是一只樟木箱,静静待在老街深处的一座老宅里,陪着这个家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。我的身子是上好的樟木打造,表面的红漆已经褪得斑驳,边角处磕碰出的凹痕里,藏着一茬又一茬人的故事。
我出生在 1950 年的春天,那时候江南的木工作坊里,锯子和刨子的声响能飘出半条街。打造我的木匠师傅姓陈,手巧得很,他说樟木能防虫防潮,给家里的姑娘当嫁妆,再合适不过。我的第一个主人是陈家的小女儿阿秀,她出嫁那天,身上穿的红棉袄、头上戴的银簪子,还有她母亲传下来的绣花鞋样,都被整整齐齐地放进了我的肚子里。阿秀摸着我光滑的内壁,脸上的红晕像门口新开的桃花,她说:“往后啊,我要把孩子的小衣裳、小袜子都收在这里,让樟木的香味儿,陪着他们长大。”
后来,阿秀真的有了一儿一女。男孩调皮,总爱踩着小板凳扒着我的边沿往里瞧,嚷嚷着要把弹弓藏进来;女孩文静,喜欢坐在我身边,把偷偷攒下的糖纸、邮票,小心翼翼地塞进我抽屉的夹层里。那些日子,老宅的院子里总是飘着饭菜香和孩子们的笑声,我的肚子里,也渐渐塞满了带着体温的物件 —— 有孩子的奖状,有阿秀织到一半的毛衣,还有一家人难得拍的全家福。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,落在我身上,樟木的香味混着皂角的清香,在空气里慢慢漾开。
再后来,孩子们长大了,要去城里闯荡。临走那天,儿子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匣子放进我这里,里面是他攒了很久的粮票和几毛钱零钱,他说:“妈,等我挣了大钱,给你换个新箱子。” 阿秀笑着摇头,轻轻拍了拍我的身子:“不用换,这个箱子,比啥都金贵。” 那天的风有点大,吹得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沙沙响,我听见阿秀在屋里偷偷抹眼泪,我的肚子里,也多了几分沉甸甸的牵挂。
城里的日子过得快,孩子们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阿秀老了,腿脚不方便,就常常坐在我身边,摩挲着我身上的木纹,一遍遍地念叨着孩子们的小名。她把新添的孙子的小肚兜、小帽子收进来,也把自己的老花镜、针线笸箩放进我的角落。有时候,她会翻出那些旧糖纸、旧奖状,对着阳光看半天,嘴角的皱纹里,藏着笑,也藏着说不清的滋味。
又过了好些年,阿秀走了。她的儿女从城里回来,收拾老宅的东西。他们打开我的时候,一股浓郁的樟木香味涌了出来,混杂着岁月的气息。箱子里的物件,有的已经泛黄发脆,有的还带着淡淡的温度。儿子拿起那张全家福,手指轻轻拂过上面的笑脸,忽然就红了眼眶:“妈那时候,总说这个箱子是她的宝贝。” 女儿翻出那些糖纸,眼泪掉在上面,晕开了一层浅浅的水渍:“小时候,我总盼着把糖纸攒满一箱子,好跟同学炫耀。”
他们没有把我换掉,也没有把我丢弃。他们把我擦得干干净净,搬到了城里的新房子里。现在,我的肚子里,装着阿秀的孙子的毕业证书,装着他给女朋友写的情书,还装着一家人新拍的全家福。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,落在我斑驳的红漆上,暖洋洋的。
我是一只樟木箱,我没有见过外面的大千世界,也没有听过都市的车水马龙。但我见过一个姑娘的青春,见过一群孩子的成长,见过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。我身上的每一道划痕,都是时光刻下的印记;我肚子里的每一件物件,都是岁月留下的温暖。
老街的风,还在吹。老宅的梧桐树,应该又长高了吧。而我,会继续待在这个家里,守着樟木的清香,守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,慢慢变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