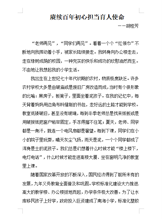老铜锁的悄悄话
我是一把老铜锁,静静躺在老家堂屋的樟木箱上,已经有七十个年头了。
我的身子是黄铜铸的,摸上去沉甸甸的,表面刻着缠枝莲的花纹,那花纹是当年锔匠师傅一锤一锤凿出来的,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时光的温度。我的锁芯是纯铜的,转起来会发出 “咔哒咔哒” 的轻响,那声音不像现在的锁具那样尖利,带着点慢悠悠的老派味道。我的小主人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她总喜欢踮着脚尖摸我的花纹,问她奶奶:“这锁里藏着什么宝贝呀?” 奶奶就会笑着拍她的头:“藏着咱们家的念想呢。”
我记得我刚被造出来的那年,是 1953 年的春天。那时候,我的第一个主人是小姑娘的太奶奶。太奶奶用红布把我包起来,小心翼翼地挂在樟木箱上,箱子里放着她的嫁衣、几匹细布,还有一串银镯子。太奶奶总说,这把锁是 “守家的”,有我在,家里的东西就丢不了,日子就能稳稳当当的。那时候,村里的日子过得紧巴,谁家有个樟木箱和铜锁,都是件值得骄傲的事。晚上,太奶奶会把门锁好,再用我把樟木箱锁上,然后坐在油灯下纳鞋底,油灯的光映着我的铜身,暖融融的。
后来,太奶奶老了,把樟木箱和我一起交给了奶奶。奶奶是个勤快的女人,她不像太奶奶那样把我当宝贝似的供着,而是真真切切地用着我。她会把家里的粮票、布票、存折都放进樟木箱,用我锁好。那时候,村里开始分田到户,奶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,晚上回来,她会打开樟木箱,数着粮票,盘算着给孩子们做新衣服。有一次,村里来了小偷,撬了好几家的门,却唯独没撬开我守着的樟木箱。小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只在我的锁身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,最后只能悻悻地走了。奶奶知道后,摸着我的划痕,笑着说:“还是老物件结实啊。”
再后来,奶奶也老了,樟木箱和我就到了小姑娘的妈妈手里。妈妈是个爱时髦的女人,她觉得我又笨又重,不如超市里卖的密码锁方便。有一次,她差点把我扔到废品站,还是奶奶拦住了她:“这锁守了咱们家三代人,不能扔。” 妈妈只好把我留下来,依旧挂在樟木箱上,只是箱子里不再放粮票和布票了,而是放着小姑娘的奖状、照片,还有一些小时候的玩具。
小姑娘慢慢长大了,从扎羊角辫的小不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考上了城里的高中,每个月才回一次家。每次回来,她都会跑到堂屋,摸摸我的花纹,然后打开樟木箱,看看里面的奖状。有一次,她拿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,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,用我锁好。她摸着我的头,轻声说:“老铜锁,你要替我守好我的梦想呀。” 我听着她的话,锁芯轻轻转了一下,好像在回应她。
现在,我依旧躺在樟木箱上,看着窗外的日升月落。村里的老房子越来越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小楼。很多人家都用上了指纹锁、密码锁,像我这样的老铜锁,已经很少见了。有时候,我会听到路过的人说:“这锁都老掉牙了,还留着干什么?” 可我知道,我不是一把普通的锁。我守着的不是金银财宝,而是太奶奶的嫁衣,奶奶的粮票,小姑娘的梦想。我守着的是三代人的时光,是一个家的念想。
夜深了,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身上,黄铜的表面泛着淡淡的光。我好像又听到了太奶奶纳鞋底的声音,听到了奶奶盘算日子的声音,听到了小姑娘的笑声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变成了一首温柔的歌,在堂屋里轻轻回荡。
我是一把老铜锁,我守着一个家的故事,守着时光的温度。我知道,只要樟木箱还在,只要这个家还在,我就会一直守下去,守着那些藏在锁芯里的悄悄话,守着那些永不褪色的念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