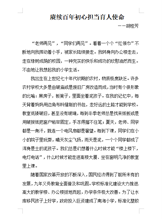巷口糖画摊,甜了旧时光
清晨的风裹着巷子里油条的香气,溜过青石板路的缝隙,我揣着兜里的五块钱,一颠一颠地往巷口跑。那里有个糖画摊,守摊的是个姓陈的老爷爷,我们都喊他陈爷爷。这是我每天放学最盼着的地方,也是这条老巷子里,藏着最多人情味的角落。
我读初二,家就在巷子深处的老楼里。这条巷子里的房子,墙皮都有些斑驳了,墙角的青苔长了又落,落了又长,就像陈爷爷的糖画摊,在巷口摆了十几年,从来没挪过地方。陈爷爷的摊子很简单,一个小木桌,上面摆着熬糖的小锅,一把长柄的铜勺,还有一块光溜溜的青石板。木桌的一角,插着几根已经做好的糖画,有龙有凤,有小兔子,还有孙悟空,在阳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,看得人眼睛都直了。
第一次买糖画,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。那天放学,我攥着妈妈给的一块钱,站在摊前挪不动脚。陈爷爷看我盯着那只糖兔子,笑眯眯地问:“小丫头,想要哪个呀?” 我怯生生地指着兔子,他点点头,拿起铜勺,从锅里舀起一勺熬得金黄的糖稀。糖稀在他手里听话极了,手腕轻轻一转,糖丝就像细得看不见的线,落在青石板上。手腕抬、落、顿、转,不过十几秒的功夫,一只耳朵长长的兔子就出现在石板上,他又用小竹签往兔子身上一粘,递给我:“拿好喽,小心烫。” 那糖画甜丝丝的,含在嘴里慢慢化掉,甜香从舌尖一直漫到心里。从那以后,我就成了糖画摊的常客。
陈爷爷的糖画,不光做得好看,还藏着不少门道。他说,熬糖稀是最关键的,火大了会糊,火小了拉不出丝,得用温火慢慢熬,熬到糖稀能拉出细细的丝,颜色变成透亮的琥珀色才行。他的手很巧,不管是飞禽走兽,还是花鸟鱼虫,只要你说得出来,他就能画得出来。有时候,巷子里的小孩围着摊子,吵着要画奥特曼,要画小猪佩奇,陈爷爷也不恼,笑着说:“你们这些小家伙,脑子里的花样就是多。” 说着,手里的铜勺就动了起来,不一会儿,一个歪歪扭扭但很可爱的小猪佩奇就成型了,惹得孩子们一阵欢呼。
陈爷爷的摊子,从来都不缺人气。放学的时间是摊子最热闹的时候,一群孩子挤在摊前,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这个要那个。陈爷爷总是不紧不慢的,一个一个地做,嘴里还念叨着:“别急别急,都有都有。” 有时候,遇到家里条件不好的孩子,站在摊前眼巴巴地看着,陈爷爷会笑着递过去一个小蝴蝶:“拿去吃吧,不要钱。” 孩子红着脸接过,小声说句 “谢谢爷爷”,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开。
有一次,我问陈爷爷:“您天天在这里摆摊,不累吗?” 他正低头熬着糖稀,火苗舔着锅底,糖稀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。他抬起头,眼睛眯成一条缝,看着巷口来来往往的人:“累啥呀,看着你们这些小娃娃吃得开心,我就高兴。” 他说,这门糖画手艺,是他年轻的时候跟师傅学的,那时候,走街串巷地摆摊,靠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。现在,日子好过了,他却舍不得放下这门手艺。“现在会做这个的人少喽,我要是不摆这个摊,怕是你们这些娃娃,都不知道糖画是啥滋味了。”
去年夏天,听说巷子要拆迁了。消息传出来的时候,巷子里的人都议论纷纷。我最担心的,是陈爷爷的糖画摊。那天放学,我跑到摊前,看到陈爷爷坐在小马扎上,手里摩挲着那把铜勺,眼神有些落寞。我小声问:“陈爷爷,巷子拆了,您还会来摆摊吗?” 他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眼前的青石板,叹了口气:“不知道啊,这老巷子拆了,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了。”
那段时间,陈爷爷的摊子前,比往常更热闹了。不光是孩子,还有很多住在附近的大人,也都来买糖画。他们说:“陈师傅,再给我做一个龙吧,小时候就爱吃您做的糖画。” 陈爷爷的脸上,又露出了笑容,他手里的铜勺,又开始在青石板上飞舞起来。
后来,巷子拆迁的事情,有了转机。听说,政府考虑到这条巷子的历史,决定保留一部分老建筑,打造成文化街区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我跑到巷口,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爷爷。他愣了一下,然后哈哈大笑起来,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:“好啊好啊,这下,我的糖画摊,还能继续摆下去了。”
现在,陈爷爷的糖画摊,还在巷口的老地方。经过改造的巷子,比以前更漂亮了,新铺的青石板路,两旁的老房子修旧如旧,还多了不少新的店铺。但陈爷爷的糖画摊,还是老样子,小木桌,铜勺子,青石板,还有那个笑眯眯的老爷爷。放学的时候,依旧有一群孩子挤在摊前,吵着要糖画。阳光洒在青石板上,糖画的甜香飘满了整条巷子。
我知道,陈爷爷的糖画摊,不仅仅是一个卖糖画的地方,它更像是一个小小的港湾,装着我们这些孩子的童年,装着老巷子里的人情味。那些金黄的糖画,甜了我们的舌尖,也甜了那些慢慢流淌的旧时光。我想,等我长大了,也会带着我的孩子,来到这个巷口,买一只糖画,告诉他,这里曾经有一个老爷爷,用一把铜勺,画出了整条巷子的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