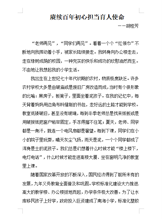竹筛里的光阴
我是一把竹编筛子,栖身在老家堂屋的八仙桌底下,浑身裹着一层薄薄的时光尘埃。篾条交织的纹路里,藏着爷爷指尖的温度,也藏着一门老手艺的兴衰流转。
我的骨架由三年生的毛竹削成,那些竹篾细得像发丝,却坚韧得能扛起岁月的重量。记得诞生那天,后院的竹影斜斜地铺在青石板上,爷爷坐在小马扎上,手里拿着锋利的篾刀,先将粗壮的毛竹劈成两半,再顺着竹纤维一点点剖成细篾。“咔嚓、咔嚓” 的声响里,竹屑簌簌落下,带着新鲜竹子的清香。爷爷的手指粗糙,指关节处布满老茧,却灵活得不像话,他把篾条在温水里泡软,再用刮刀细细打磨,直到每一根都光滑温润,摸起来像婴儿的肌肤。
“编筛子要心细,篾条要齐,纹路要匀,不然筛不出好粮食。” 爷爷编到兴起时,会对着蹲在旁边的父亲念叨。我看着他的手指在篾条间穿梭,时而交叉,时而缠绕,时而提拉,原本零散的篾条,渐渐在他手中形成了规则的菱形纹路。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洒下来,照在爷爷花白的头发上,也照在我逐渐成型的身上,那些交错的篾条在光影里忽明忽暗,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整整三天,爷爷才把我完成,最后在我的边缘缠上一圈结实的竹边,用细麻绳牢牢固定。那一刻,我成了一把真正的竹编筛子,带着竹子的清香和匠人的心意,站在了灶台旁的木架上。
那时的我,是家里的 “功臣”。每年秋收后,奶奶都会把晒干的稻谷倒进我的怀里,轻轻摇晃。饱满的谷粒从我的纹路间落下,瘪谷和杂质则被留在筛面上,被奶奶轻轻拂去。筛谷的声响沙沙作响,混着奶奶的唠叨和院子里鸡犬的鸣叫,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。邻里们也常来借我去用,每次送回来时,都会带着一碗刚蒸好的红薯,或是几个新鲜的鸡蛋,笑着说:“你家这筛子编得好,结实又好用,比集市上买的塑料筛子强多了!” 爷爷听了,总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再拿起抹布,细细擦拭我身上的谷糠。
后来,父亲渐渐接过了爷爷的篾刀。爷爷站在一旁指导,父亲的动作起初有些笨拙,常常把篾条弄断,手上也被篾刀划出道道血痕。爷爷不说话,只是把自己的手递过去,让父亲摸那些老茧:“学手艺哪有不受伤的?多练练就熟了。” 父亲咬着牙,日复一日地练习,手指慢慢变得灵活,编出来的筛子也越来越像样。我看着父亲编出的那些筛子被陆续送到邻居家、集市上,看着竹编手艺在父子间传递,心里满是欢喜。那时的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,竹香会永远萦绕在这个小院里。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一切都变了。集市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塑料筛子、不锈钢筛子,它们价格便宜,制作快捷,很快就占据了市场。人们渐渐不再需要爷爷和父亲编的竹筛子了,那些曾经来借筛子的邻居,家里也换上了崭新的塑料筛子。后院的竹子长得越来越茂盛,却再没有人去砍伐、剖篾。爷爷的篾刀生了锈,父亲的手指也渐渐生疏,家里的竹编手艺,就像被遗忘在角落的我一样,蒙上了厚厚的尘埃。
爷爷去世那天,父亲把我从木架上取下来,细细擦拭干净。他的动作很轻,仿佛怕碰碎了什么珍宝。“爸,您放心,这手艺我没丢。” 父亲对着爷爷的遗像喃喃自语,眼里含着泪水。从那以后,父亲一有空就会坐在后院的小马扎上,重新拿起篾刀剖竹、编筛。起初,他的动作很生疏,编出的筛子也不如从前精致,但他没有放弃,一点点回忆着爷爷的教导,一点点摸索着技巧。
去年夏天,村里来了一群写生的大学生,其中一个女孩发现了父亲编的竹筛子,兴奋地叫了起来:“哇,这竹编好漂亮!是老手艺吧?” 女孩的叫声吸引了其他人,大家围着父亲编的竹筛子,不停地拍照、询问。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他耐心地给大学生们讲解竹编的技巧,演示编筛子的过程。那天,父亲编的三个小竹筛子被大学生们买走了,他们说要带回去做纪念,还要把这门老手艺分享给更多人。
从那以后,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村里有位会竹编的手艺人。有人专门来买竹筛子,有人来学习竹编手艺,后院的竹香又重新飘了起来。父亲还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竹编培训班,教村里的老人和妇女编竹筛子、竹篮、竹席。他常说:“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,只要有人愿意学,我就愿意教。”
我依旧守在堂屋的八仙桌底下,看着父亲带着学员们剖篾、编织,听着熟悉的 “咔嚓” 声和欢声笑语。阳光依旧透过屋檐的缝隙洒下来,照在那些交错的篾条上,也照在我的身上。我知道,爷爷的手艺没有失传,那些藏在篾条里的匠心和温度,正在被一代代传递下去。
竹筛里的光阴,慢悠悠地流淌着,带着竹子的清香,也带着非遗手艺生生不息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