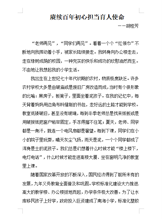木梳上的年轮
我是一把老木梳,身躯由温润的黄杨木雕琢而成,梳齿间还残留着百年前阳光的气息。我的主人是苏家木梳的第三代传人,如今卧在樟木箱底,听着窗外的蝉鸣,思绪总能飘回那些刻满木屑与茶香的日子。
我的制作者,也就是苏家的老爷子,是个沉默寡言的匠人。记忆里,他总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,面前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木块、砂纸和刻刀。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洒下细碎的光斑,也照亮他指尖的薄茧。老爷子选木极严,非要用生长了二十年以上的黄杨木,说这样的木材温润坚韧,梳头发不伤头皮。他会把木块放在鼻尖轻嗅,像在与老树对话,确认木材的纹理与湿度,稍有瑕疵便弃之不用。
我诞生的那天,院子里飘着淡淡的茉莉花香。老爷子先将选好的黄杨木切成合适的尺寸,用粗砂纸反复打磨,直到木块表面光滑得能映出他的皱纹。接着,他用细针在木头上勾勒出梳齿的形状,每一道线条都笔直均匀,仿佛早已刻在他的心里。刻刀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,时而轻柔如蝶翼点水,时而沉稳如泰山压顶,木屑随着刻刀的起落纷纷扬扬,像一场金色的小雪。我亲眼看见他为了让梳齿间距精准,反复测量了十几次,哪怕只有一丝偏差,也会重新打磨。
“做木梳,做的是手艺,更是良心。” 这是老爷子常说的话。他给我雕刻梳背时,选了 “松鹤延年” 的纹样,仙鹤的羽翼、松树的针叶,每一处细节都栩栩如生。最后一道工序是上蜡,他用棉布蘸着自制的蜂蜡,一遍遍擦拭我的身躯,直到我浑身泛起温润的光泽。完工时,老爷子把我捧在手心,眼底是藏不住的欣慰,他轻轻摩挲着我的梳背,低声说:“以后,就拜托你陪着丫头了。”
丫头是老爷子的孙女,也是我的第一任主人。她第一次见到我时,眼睛亮得像星星,小心翼翼地接过我,用我梳理她乌黑的长发。丫头总爱趴在老爷子的工作台边,看他制作木梳,时不时问些天马行空的问题。老爷子从不嫌她烦,会放慢动作,给她讲解每一道工序的要领。“梳齿要打磨三十遍,少一遍都不行,这是苏家的规矩。”“上蜡要顺着木纹,就像顺着人心走,不能急。” 丫头似懂非懂地点头,小手却已经拿起了最小的刻刀,在废弃的木头上模仿起来。
后来,丫头长大了,要去城里读书。临走那天,老爷子把我塞进她的行囊,再三叮嘱:“木梳要常保养,就像手艺不能丢。” 丫头抱着我,眼泪掉在我的梳齿上,冰凉冰凉的。在城里的日子,丫头每天都会用我梳头发,梳齿划过发丝的触感,总能让她想起老家的院子和老爷子的身影。假期回家,她总会第一时间跑到工作台前,跟着老爷子学做木梳。她的手法从生疏到熟练,指尖也渐渐长出了薄茧,老爷子看她的眼神,满是欣慰与期许。
可时代变得真快啊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塑料梳子、电动梳子摆满了商店的货架,精致又便宜,人们渐渐忘了我们这些手工木梳。苏家木梳的生意越来越冷清,工作台前的木屑也渐渐积了灰。老爷子的身体越来越差,却还是每天坐在老槐树下,摩挲着那些半成品的木梳,眼神里满是落寞。丫头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她尝试着把苏家木梳的制作过程拍下来发到网上,没想到,那些细腻的工序、温润的木材,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
有人开始向丫头订购手工木梳,有人专程来家里拜访老爷子,想学这门手艺。老爷子重新燃起了精神,和丫头一起,把工作台收拾干净,又开始了忙碌的日子。丫头还根据年轻人的喜好,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,设计了一些新颖的图案,让老手艺有了新活力。我看着丫头像当年的老爷子一样,认真地选木、打磨、雕刻,看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刻刀,看着苏家木梳的香气飘得越来越远,心里满是欢喜。
如今,老爷子已经不在了,但他的手艺留了下来,他的话也留了下来。丫头成了苏家木梳的第四代传人,她把老爷子的工作台收拾得干干净净,每天都在院子里制作木梳,老槐树下的阳光,依旧温暖如初。我虽然老了,梳齿也有些磨损,但丫头依然把我珍藏着,偶尔拿出来摩挲一番,就像当年老爷子对她那样。
我知道,我不仅仅是一把木梳,更是一段岁月的见证,一份手艺的传承。那些刻在我身上的纹样,是匠人的坚守;那些留在我身上的温度,是亲情的延续。只要还有人记得手工木梳的温润,只要还有人愿意传承这门手艺,苏家木梳的故事就会一直继续下去,就像老槐树上的年轮,一圈又一圈,永不消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