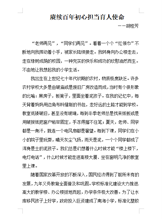一张旧藤椅的独白
我是一张旧藤椅,如今蜷缩在老家阁楼的角落,身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,腿上还缠着一道早就褪色的布条。若不是前几天小主人翻找旧物时踢到了我的腿,恐怕我还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,继续沉睡下去。
我的记忆,是从七十多年前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开始的。
那时候,我还不是现在这副老态龙钟的模样。我的骨架是上好的楠竹,藤条是山里采来的青藤,被村里最手巧的篾匠叔叔,一匝一匝、一针一线地编织起来。篾匠叔叔的手很粗糙,却格外温柔,他说:“这藤椅要坐一辈子的,得结实。”
我的第一个主人,是小主人的太爷爷。那时候太爷爷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,刚刚成家,用攒了大半年的工钱,把我从集市上买了回去。他把我安放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,每天收工回来,总要先坐在我身上歇一会儿,摸一摸我光滑的藤面,再点上一袋旱烟,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,嘿嘿地笑。
太奶奶那时候还是个俏姑娘,总爱倚在我的扶手上,一边纳鞋底,一边听太爷爷讲田里的趣事。阳光透过窗棂,洒在她乌黑的发梢上,也洒在我身上,暖洋洋的。偶尔,太爷爷会伸手,轻轻拨弄太奶奶垂下来的发丝,我能感受到他们靠在一起时,那种淡淡的、甜甜的欢喜。
后来,小主人的爷爷出生了。他是个调皮的小家伙,刚学会走路,就喜欢绕着我转圈跑,还总爱撅着屁股,想爬到我的背上。有一次,他脚下一滑,摔在了我的腿上,疼得哇哇大哭。太爷爷赶紧把他抱起来哄,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腿,嘟囔着:“这椅子跟着我这么多年,都摔出感情了。” 那天晚上,太爷爷找了块布条,小心翼翼地把我磕伤的腿缠了起来,就是现在我身上这道褪色的布条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石榴树长高了,结了一茬又一茬的石榴;太爷爷的头发白了,背也渐渐驼了;而我,也开始慢慢变老。我的藤条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柔韧,坐上去会发出 “咯吱咯吱” 的声响,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再后来,小主人的爸爸也出生了。他不像爷爷小时候那样调皮,总爱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上看书。那时候,村里还没有通电,晚上就点一盏煤油灯。昏黄的灯光下,爸爸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,映在墙上,也映在我身上。我陪着他,从《三字经》读到《水浒传》,从懵懂孩童长成翩翩少年。
等到小主人出生的时候,家里已经添了新的沙发、新的椅子,我被挪到了角落里。小主人小时候,也喜欢爬到我身上玩,她的小手胖乎乎的,摸在我的藤条上,软软的。她总爱问奶奶:“这椅子怎么这么旧呀?” 奶奶就会笑着说:“它呀,是家里的老宝贝,比你太爷爷的岁数都大呢。”
后来,家里盖了新房子,爸爸妈妈要把老房子里的东西都扔掉,说我又旧又破,占地方。是奶奶执意要把我留下来,她说:“这椅子陪了我们家四代人,扔了可惜。” 于是,我被搬到了阁楼,一待就是好多年。
阁楼里很安静,只有风吹过瓦片的声音,还有老鼠偶尔跑过的窸窣声。我常常在想,我是不是就这样,在灰尘里慢慢腐朽,直到被人彻底遗忘?
直到前几天,小主人翻找旧物时,发现了我。她蹲下来,轻轻拂去我身上的灰尘,摸着我腿上的布条,问奶奶:“这布条是怎么回事呀?” 奶奶就给她讲起了太爷爷、爷爷、爸爸的故事,讲起了那些我陪他们走过的岁月。
小主人听完,眼睛亮晶晶的。她小心翼翼地把我擦干净,又找了块新布条,把我磕伤的腿重新缠好。她说:“这椅子真有意思,它见证了我们家四代人的故事呢。”
现在,我被小主人搬到了她的房间里。每天阳光照进来的时候,她就会坐在我身上看书、写字。我又能感受到那种暖暖的、甜甜的气息,就像七十多年前,太爷爷和太奶奶靠在我身上时的那样。
我知道,我已经很老了,我的藤条会越来越松,我的骨架会越来越脆。但我不害怕,因为我知道,我不是一张普通的藤椅。我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者,是一个家庭的记忆载体。我承载着太爷爷的汗水,太奶奶的温柔,爷爷的调皮,爸爸的书卷气,还有小主人的欢声笑语。
这些记忆,就像一颗颗饱满的石榴籽,被妥善地收藏在我的身体里,永远不会褪色。